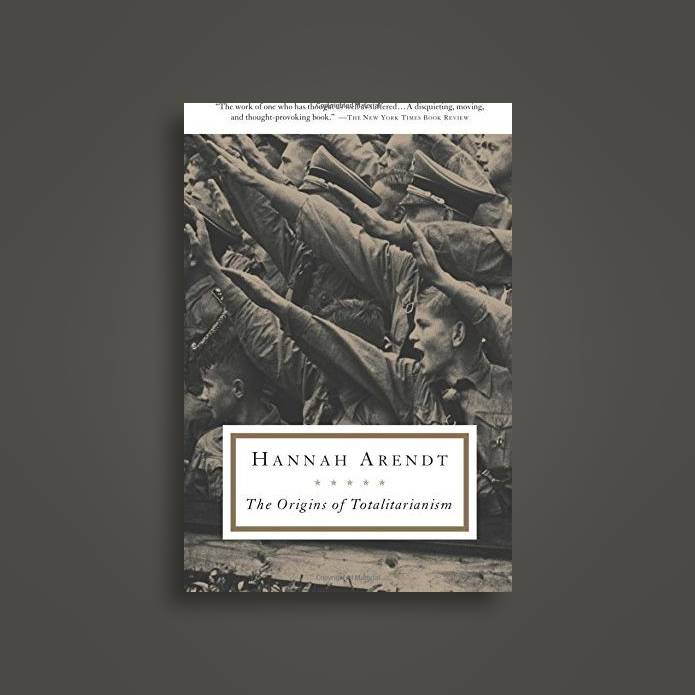
被孤立的「一個人」
鄂蘭根據當時流出海外的蘇聯原始檔案(Smolensk Archive,即斯犘蘭檔案,1941年德軍侵俄時擄獲,戰後落入美國手中;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當局証實其真確性,並於2002年歸還),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即是蘇聯建政約十年後左右,雖然不論鄉村的農民,還是城市的工人,皆「普遍有不滿的情緒」,但蘇聯境內業已欠缺「有組織的反對力量」(第13頁)。
在第268頁,鄂蘭有更詳盡的解說:「在全面恐怖的局勢底下,人與人之間溝通的界線和孔道被一鋼鐵的箍條所取代,透過這條鋼鐵箍條的壓制,人世間多元、繁複的景象好似消逝無跡影,而變成一巨大的,宛如祇有一個人存在的單調景觀(之後稱之為「單一的人[One Man,第270頁]」)……迫使每一個人彼此鬥爭,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它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空間……」
我們望望深圳河以北,此種蘇聯模式,獲得完美複製,而且說得上是青出於藍。甚至因為時空的優勢,還可再加補充──他們已經無法了解自由的真義,以為等如為所欲為,以致他們來港或外遊,特別是一些自由國家,往往醜態百出。再看看蔡英文博士,如何引介她對鄂蘭的觀察:「『權力』不祗是意指人行為的權力,也意涵『共同做事』(to act in concert)能力……祗有在一群人結合起來共同為某種目標……奮鬥時,才可形成『權力』……(那)是與他共事的群體賦予他的……」
抗共三十年的省思
極權政體集團成員,為了維持權力與集體概得利益,有一起「共同做事」打壓異議人士與團體的動力(與他們因權力與利益分配不勻而內鬥,並無矛盾)。反過來說,對抗極權的各方異議團體,當然也為了改變不義的現狀而「共同做事」,當權者拒絕交出權力,就對抵抗者拖加鎮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異議者,大多因此流亡海外,成為海外民運人士。他們到達自由世界,各自建立組織抗共,如今卻分崩離析,就當然有美國對華戰略失誤的因素,令中共有打三十年持久戰的本錢;海外民運人士組織團體,及發生內部分歧而另起爐灶,其實也是一種民主實踐,但十分不幸,他們在這方面的表現慘不忍睹。
而在香港,我們處於一個完整的民主政制,卻有一定的議會席位,供有志者角逐,而爭取全面民主的各路政團,當然亦優而為之。既然組織海外民運團體,是民主實踐,那麼參與虛擬局部議會政治,也不會例外。民主與專制與極權的分別,主要在於對異議者的態度,及是否會搞統一思想。香港在野各方陣營,同樣是不及格,而且當中有不少情節,我們之中不少人,或多或少都有參與其中,雖說西諺有云:「兩個人才跳得成探戈」而且問題主要出自主流派,但我方總要負上一點責任。
反過來說,香港在野陣營要重建互信,到今天恐怕已是知易行難。不過,相信讀者閱覽此段時,要麼極權體制已在香港落地生根,要麼即使政府收回《逃犯條例》,他們及其背後的北京主子,也會找別的機會,奪去香港餘下的自由。所以我們要珍惜餘下的政治伙伴關係,勿再輕言反目,教當權者可輕易打散彼此間的連繫,令每個人成為原子化的存在,等著被逐個擊破與奴役 - 這也是「進德修業」的其中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