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我們都會為藝術家籌備演出,以及不同的活動。今年的疫情對我們或多或少有影響。希望疫情盡快平息,一切重回正軌,讓一眾會員能重拾發展空間。」香港展能藝術會主席林彩珠(Ida)說。
展能藝術會是全港唯一全方位開拓展能藝術的機構,並有社會企業「藝全人」(ADAM),連繫展能藝術家與商業機構,協助他們開闢商機,卻至今都沒有獲港府恆常資助,「一般獲得恆常資助的機構,日子過得比較輕鬆;我們則是就每個項目去申請資助。坦白說,不是每一次都成功;而且每次資助的金額又不同,因此做每一個決定都必須非常謹慎,亦要努力籌錢 - 既要做好本份,又要時刻為稻粱謀,人手及資源又如此有限,難免心力交瘁。」
她表示:「如果同事可以專注份內事,果效定必不一樣!目前環球局勢風高浪急,私人公司的基金,或會因為公司生意自顧不暇而收緊資助額。若情況持續惡化,我們現有的計劃與及服務都會受影響。」
「財爺陳茂波在《二零二零/二一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到,2019至2020年政府投放在文化藝術的總開支逾五十億,當中有幾多撥作展能藝術發展?我們的展能藝術家,都是香港市民,亦為社會一份子,希望有平等的發展機會 - 我認為,政府必須要有長遠而且具體的支援!」
發展藝術才華,亦屬殘疾人士的復康服務
瘟疫政治下,各行各業都受極大影響,包括演藝界 - 當位於東涌、擁有超過七萬平方米可租用面積的亞洲博覽館都改建成「方艙醫院」,而各社區會堂、社區中心等都被用作社區治療設施;同時口罩令、限聚令又繼續維持,香港的演藝界,只有三個選擇:取消、延期或網上舉行。
雖然近期港府有逐步放寬各種禁令之趨勢,但其實在2020年,大部份的表演與及舞台演出都因為港府所頒佈的禁令而無法如期舉行,不論四面台的演唱會,或社區中心裡的小型表演,無一不受打擊。為此熱血時報找來香港展能藝術會主席林彩珠(Ida),談談疫情對他們的影響。
「每年我們都會為藝術家籌備演出,以及不同的活動。今年的疫情對我們或多或少有影響。然而以我所知,不少機構或公司舉辦比我們的更大的規模演出,他們所承受的壓力與打擊或許更大!希望疫情盡快平息,一切重回正軌。香港展能藝術會(簡稱展能藝術會,或ADAHK)一向推廣社會共融,期望一眾會員能重拾發展空間。」
先介紹一下背景。展能藝術會以「藝術同參與,傷健共展能」為宗旨,至今仍是全港唯一全方位開拓展能藝術的機構;每年辦多場演出及展覽,並有社會企業「藝全人」(ADAM),連繫展能藝術家與商業機構,協助他們開闢商機。機構成立後不久,Ida即加入成為一員,至今是展能藝術會的主席。「我們相信殘疾人士都有權發揮藝術才華,亦有權如一般人般參與創作及欣賞藝術。」
「上世紀八十年代,殘疾人士的復康服務以即時滿足其基本需要為主,如讀書、生活技能、職前訓練等,旨在讓他們可以獨立生活。那年頭最重要『有飯食、有書讀』,對他們來說藝術既是奢侈,也是遙不可及的事。至於我們的理念,一如展能藝術會的英文名『Art with the Disabled Association』,不是『For Disabled』或『By Disabled』,要與他們同心、同行,不分你我 -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來說相當前衛。」
初成立時並沒有同事,只有一班熱心會員
「我加入了社會服務聯會(簡稱社聯)的復康服務部(Rehabilitation Service)後,首個參與的項目就是國際展能藝術節。其時,大會請來世界各地的展能藝術家來港表演,有歌舞、默劇、展覽等。有趣的是,這些演出和展覽,都由傷健人士主導,而無論是否殘疾人士,都一樣可以欣賞。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般人眼中的展覽只可遠觀,還有『請勿觸摸』的警告牌;但當時卻有一個可被觸摸的展覽,讓失明及視障人士都可以欣賞作品。」她笑言自己當年「矇查查」,並沒有細想活動的意義,但見台前幕後均樂在其中,因此印象非常深刻。
「還記得那年頭,身邊不少朋友,從未去過香港的藝術演出場地,又有從未入場欣賞過舞台演出、對藝術沒有概念的人。活動完滿結束後,大家都得到啟發,驚覺『原來可以咁樣!』我們認為,如此有意義的事,不應只是一個獨立項目,必須要承傳、發展。」就這樣,香港展能藝術會於1986年11月成立。
「那時候,當社聯有新項目或服務時,相關的負責同事都會參與籌備。完成後,若新項目成立了機構,這位同事就會成為當然委員。當日以社聯同事身份加入國際展能藝術節籌備委員會(Organizing Committee),香港展能藝術會成立後,包括我在內在的所有委員,都成為了管理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成員;而我則是當然委員。來到今日,仍有不少委員與成員與我一樣,由創會初期加入至今。」
展能藝術會成立後兩年,即1988年,與國際展能藝術會(Very Special Arts,後易名VSA)聯網,增加與世界各地的展能藝術家及團體交流的機會。Ida表示,展能藝術會初成立時,並沒有同事,只有一班熱心會員。
她又憶述第一次辦活動的情景:「選址維多利亞公園,籌辦得十分粗淺!我們把物資放在紅白藍膠袋內,每人拿一兩袋到場,然後忙了一整日,很累但滿足。印象裡,當日還有輪椅舞呢!後來,有慈善團體表示願意借出一角給我們作辦公室,令展能藝術會的發展漸趨穩定,亦聘請了第一位同事。」來到今日,在各方基金及團體支持下,展能藝術辦「藝無疆」計劃,並於五年前成立了社企「藝全人」,服務亦變得多元化。「除了總辦事處外,又有位於石硤尾JCCAC的『賽馬會共融藝術工房』、『藝術通達服務中心』等;此外更成為不少NGO及藝術單位的合作夥伴,都是大家努力的成果。」
慨嘆來到廿一世紀,殘疾人士出路仍有局限
一般社福機構定期搞活動、開展不同計劃與項目,都是「手板眼見功夫」;Ida強調,看來簡單的事,在同事眼中,皆是挑戰。「即使一切就緒,而且安排妥當,但都不代表活動能夠成功舉辦。曾經有殘疾人士表示很希望參加我們的活動,無奈由出門到復康巴士的一段路,必須要有人同行並提供協助;又有失明人士在計劃舞台演出時期望使用『威吔』,並於舞台上來回走動 - 大家眼中是輕而易舉的事,頂多做足功課或排練數次就可以,但對他們來說,處處是難關。因此,每一次舉辦活動時,同事們必須計劃周詳,並要有充足的人手;而這都是其他人難以想像的,」
相信不少人都知道,石峽尾的JCCAC裡有不少藝術單位,但原來這裡有一個以展能藝術為主題的空間「賽馬會共融藝術工房」,年中無休地讓大眾近距離接觸展能藝術家的作品。「我們不時與JCCAC的『鄰居』合辦展覽、活動及課程。我們曾與JCCAC內的一位陶藝家合作,請他來辦陶藝班,讓我們的藝術家、會員與家人一同參與,齊齊享受陶藝的樂趣。」
提到籌辦活動,或許會以為,不外都是演出或展覽吧?其實不然。「橫空出世的藝術家,當今世上沒有幾個。對於傷健人士,我們提供合適的土壤,讓他們可以發展藝術才能。多年來,每年一度的『藝無疆』計劃,主題以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交替,旨在透過公開比賽,發掘有潛質的展能藝術家,同時讓大眾有機會欣賞他們的精彩演出及作品。比賽不是『圍威喂』式閉門造車,而是向各間特殊學校以及公眾人士發出邀請;無論視覺或表演藝術,會分不同類別如青少年組、團體組及個人組等,並會辦一場總決賽,入場人士更有份投票!」Ida表示,勝出者可獲得書劵或獎學金,同時展能藝術會亦為他們提供度身訂造的培訓計劃,並有獨立展覽及演出活動;另外又有機會代表香港參與國際展能節(International Abilympics),與世界各地的展能藝術家交流。
「今時今日,一般人想發展藝術亦不容易,更別說傷健人士!栽培展能藝術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細水長流,給予時間、空間與土壤,讓他們有機會發光發亮。社企『藝全人』幫助他們與世界接軌,有機會與其他社福機構或私人公司合作,既能以自己專長獲得收入,同時開拓公眾視野 - 本地的展能藝術家的演出及作品,亦相當有水準!『藝全人』有『常駐藝術家』、『展能藝術天使』及『青葉藝術家』,他們的經歷不同同時各有專長,而且多次到外地交流並獲得本地及海外的藝術獎項。」值得一提的是,曾接受熱血時報訪問的音樂家蕭凱恩(Michelle)及攝影師鄭啟文(Kevin),亦是展能藝術會的「展能藝術天使」一份子。
Ida慨嘆,即使在廿一世紀,殘疾人士的出路,依然相當局限。「即使擁有大專甚至大學程度,傳統上他們的出路亦不多;或因為這個緣故,致使他們與及家人都難以想像,可以透過藝術發展而自立。我們思前想後,掙扎了一段日子,終在五年前成立『藝全人』,透過提供藝術演出、藝術圖像、委任創作、商務禮品及產品推廣等服務,為本地展能藝術家創造工作機會及收入來源。」她強調,更重要的是,他們有奮鬥目標,並成為大眾的榜樣與楷模。
展能藝術家亦值得獲恆常資助 冀政府有長遠而且具體的支援
「他們的成功,一是仰賴自身的才華與努力,若是貪懶的人或怕辛苦,意志不夠堅定的人,難成大事;其次是家人與師長的栽培 - 有時候長輩會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認為糊口要緊。若他們抱持開放的胸襟,讓殘疾人士有機會接觸藝術,甚至發揮創意細胞,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至此,展能藝術會則是一個平台,讓他們有機會一展所長,並以此賺取收入。」常說藝術不能以金錢衡量,Ida認為,應是「藝術不能單純以金錢衡量」才對。
「展能藝術家們做自己擅長的事,並以之賺取收入,從而達到生活自主,是一件美事呀!他們的作品,背後意義比金錢更為重要!」
來到2020年,展能藝術會成立逾卅年,Ida回望過去,感受良多。「若以人類做比喻,三十年來所經歷的,是不同的成長階段。一開始時的是萌芽階段,然後慢慢去孕育自己、成長,接下來站穩腳步......一步一腳印,每個階段都不容易。我們的項目,不一定得到政府與及社會人士的認同和接受;我們至今都沒有獲港府恆常資助,全都是逐個項目或計劃去申請,因此我們必須不斷努力。」
她又提到,展能藝術會每年舉辦的「藝無疆」,至今成為了不少特殊學校及社福機構的「藝術催化劑」。「展能藝術會是全港唯一提供全方位藝術發展的機構,任何殘疾人士都可以參加,並與VSA有聯繫,默此可以邀請海外富經驗的藝術家來港辦工作坊 - 在讓大家享受藝術創作樂趣之同時,亦有為特殊學校及相關社福機構的教職員提供培訓,使他們認識並開始重視此一範疇,再將之帶回學校,讓學生受惠。多年來,『藝無疆』的水平一直提升,最重要的原因是特殊學校願意發掘同學的才華,甚至聘請經驗豐富的導師去栽培有天份者,然後參與我們的賽事。在良性競爭下,整體水平自然得以提升。同時,我又留意到,其他機構都有辦類似的項目,可謂百花齊放!」
「至於『藝全人』 - 歷史與經驗告訴我們,辦社企不容易,而且成功率不高。一般所能申領資助的項目都以三年為限,因此第二年伊始,已為下一次申請資助而煩惱。老實說,當時我們想到,廿多年來,每辦一項活動都不容易,應否再另立社企?倘若社企成立後一直虧本,又怎麼辦?不過,每次看到展能藝術家們的超水準演出及作品,卻苦無發展機會;他們又時刻流露『夢想成為藝術家』的想法,都令我們都感到心痛,不斷反思:若真心相信他們的才華,就應當製造機會,以讓他們有更好的發展、有更大成就!不是說『藝術無疆界』嗎?傷健人士不一定永遠都是接受服務與支援的一方!他們值得並且有能力,憑著無人可以取代的專長,在藝術界別中獨當一面,甚至得到豐厚回報,養活自己與家人。」她又感恩不少本地企業與集團的基金會,如太古集團、賽馬會及利希慎基金等,一直默默支持展能藝術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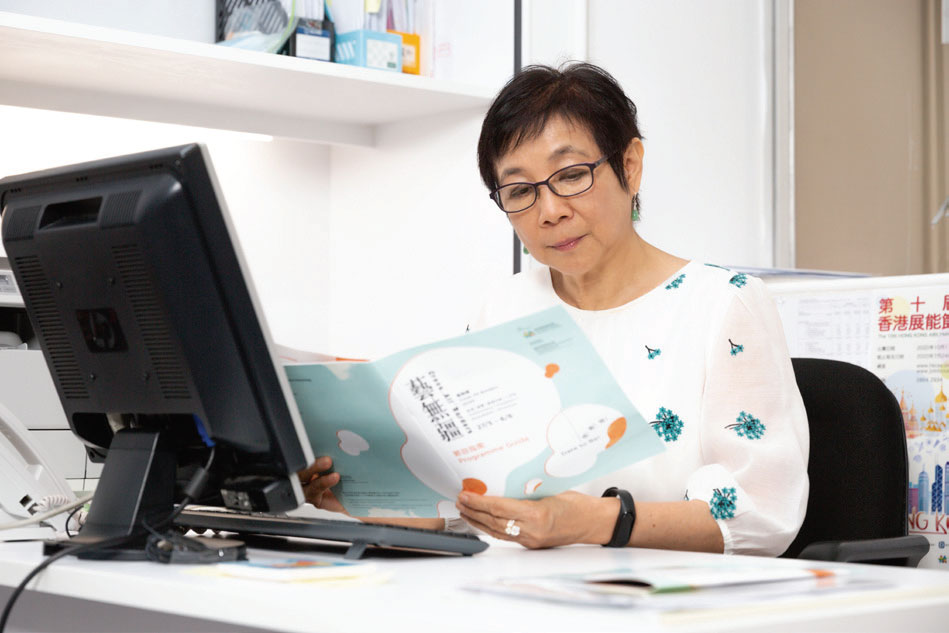
2020年的武漢肺炎疫情,Ida認為對於會員及參加者而言亦有好的一面,並非全屬壞影響。「雖然我們的項目及計劃都要延期或改於網上舉行,但我留意到,影響不是一面倒的負面。譬如,一眾不良於行的朋友,可以足不出戶地參加網上的工作坊及分享會,即使打風落雨,亦可如期舉行。又有同事向我反映,自閉症的朋友們非常享受宅在家的日子 - 平日要他們到指定地點上課或參加活動,對家人來說或是負擔;但能夠留在家裡透過網絡與大家聯繫,大大減低了他們與及家人的壓力!由是他們有更多發展空間,亦不受各種環境影響,創意自然更加澎湃,亦做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實在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亦使我們去思考更多的可能性。」
聽來展能藝術會的發展都很順暢,Ida卻搖頭。「才不!雖說疫情過後,一切將回復正軌,但其實『機會』從來都是個問題。一般的家庭,小朋友想學彈琴 跳舞或唱歌,問題不大;但對於殘疾人士來說,情況就截然不同。即使得到他們的家人首肯,即使他們極具天份,亦不一定在本地找到合適的導師 - 以Michelle為例,她才華橫溢,父母亦非常支持她,卻難以找到一位盡心培育她,而且有豐富教失明人士彈琴的導師,同時要找點字樂譜十分困難。我們一直與VSA有聯繫,深知不少外國的政府,願意撥出大量資源去支持殘疾人士發展藝術,並且有不少成功個案。反觀『亞洲國際都會』的香港,政府應當在這方面撥出更多資源。」
「一般獲得恆常資助的機構,日子過得比較輕鬆;我們則是就每個項目去申請資助。坦白說,不是每一次都申請成功;而且每次資助的金額又不同,因此做每一個決定都必須非常謹慎,亦要努力籌錢 - 既要做好本份,又要時刻為稻粱謀,人手及資源又如此有限,難免心力交瘁。如果可以專注份內事,果效定必不一樣!目前環球局勢風高浪急,私人公司的基金,或會因為公司生意自顧不暇而收緊資助額。若情況持續惡化,我們現有的計劃與及服務都會受影響。」
她又慨嘆:「我們一直努去說服政府,展能藝術會與其他的藝術團體,一樣值得獲得恆常資助;但財爺陳茂波在《二零二零/二一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到,2019至2020年政府投放在文化藝術的總開支逾五十億,當中有幾多撥作展能藝術發展?我們的展能藝術家,都是香港市民,亦為社會一份子,希望有平等的發展機會 - 我認為,政府必須要有長遠而且具體的支援!」
「在過去的日子,不少人或會認為直接捐錢到提供服務的機構已經足夠;至於『搞藝術』,是吃飽飯後才做的事吧,亦非生活上必須。可喜的是,大家對藝術的接受程度提升,亦願意提供更多支持、支援與空間。」她坦言,三十年來,最大的滿足感是見證不少殘疾人士,透過展能藝術會而成為藝術家,才華得以充份發揮,變得更快樂、更有自信。
「他們的狀況或是異於常人,但發展機會應屬均等。卅年來,我們都在做復康服務,期望日後的展能藝術家,不用再拘泥於身體狀況,以藝術才華在社會上獲得更多認同 - 著眼於他們的能力(ability),而不是缺陷(disability)。當這一日來臨,展能藝術會方算上軌道。」
(編按:本文刊載於熱血時報印刷版第86期。熱血時報印刷版訂閱連結:http://www.passiontimes.hk/4.0/regform.php)